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有关吗「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P83—103
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指明的新发现有四项,即“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和“元明以来大库档案”。20世纪被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如果王国维指明的四项新发现可以称之为“大发现”的话,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新发现则可以称之为“特大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山川呈瑞”,“地不
作者刘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P83—103
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指明的新发现有四项,即“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写经”和“元明以来大库档案”。20世纪被称为“大发现的时代”,如果王国维指明的四项新发现可以称之为“大发现”的话,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新发现则可以称之为“特大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山川呈瑞”,“地不爱宝”,出土文献呈“井喷”式面世,大量的甲骨、金文、战国文字资料、秦汉文字资料,尤其是层出不穷的楚简和秦汉简牍,为中国古典学研究带来连绵不断的新资料,促使“二重证据法”指引下的传世古代典籍的“新证研究”不断开创新局面,收获新成果。
利用出土文献对传世古代典籍进行“新证”,是出土文献研究和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有关传世古代典籍的产生和流传过程,创作时地及作者,不同文本的关系比对,用字用词习惯的考察,疑难字词的解释,思想观念的抉发,等等,都是进行传世古代典籍“新证”的主要内容。
《山海经》历来被称为“千古奇书”,在短短三万多字内容中,记载了约40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史人物和400多个神怪奇兽。其内容离奇怪诞,文辞生僻古奥,加上辗转翻刻和传抄,讹夺误衍,在在多有,留下很多有待解决的难题。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可以跟《山海经》相对照的资料,或可加深我们对《山海经》的认识,或可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理解,或可校正个别字词。这些资料在对《山海经》的进一步整理,以及探索建立利用出土文献比勘、校正和研究传世古代典籍的范式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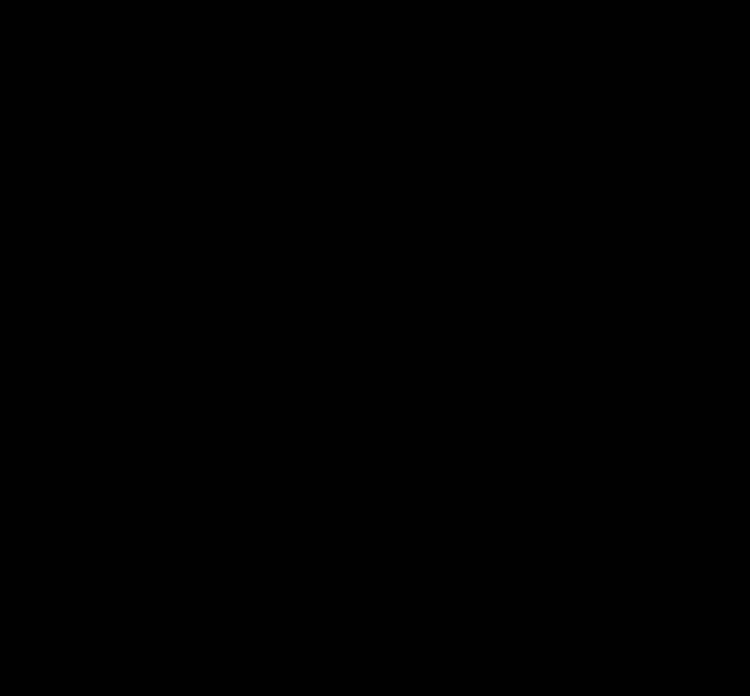
一、《山海经》的文本性质和文本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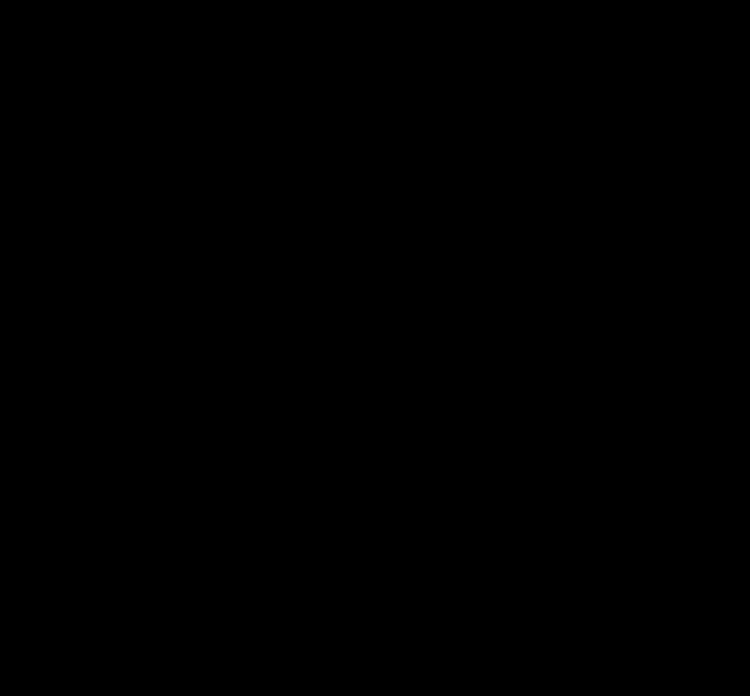
《山海经》的文本性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从古代图书分类看,历史上的《山海经》一直被给予不同对待。《汉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于数术略形法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列《山海经》于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列《山海经》于五行类,这一时期的《山海经》又被收入《道藏》,《四库全书总目》列《山海经》于子部小说家类,张之洞《书目答问》列《山海经》于史部古史类。这些不同分类既反映了不同时代对图书所呈现的知识体系认识的不同,也体现出图书分类者理解观察图书角度的不同。一个时代的图书分类,必须放到这个时代整个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去考察,才不至于以偏概全或以今律古。《山海经》内容庞杂,其内部差别也很大,譬如《山经》部分与《海经》和《荒经》部分就有很大不同,《山经》部分主要讲山川形势,林木、矿藏、动物、神怪及其实用价值和吉凶预兆,还有祭山的形式和祭品的种类。《海经》和《荒经》主要讲帝王世系、远方异国异物和神话传说。具体到《山经》《海经》和《荒经》内部,其前后内容也包罗丰富,变化不一。如果寄希望于用已有的古书类型加以比照从而将其归属于某一类,是很难得出公认的结论的。这也正是关于《山海经》的文本性质问题一直聚讼纷纭的原因所在。
古人对图书的分类和认识是个变量,是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的分类都有其背后的理据。同时任何时期的图书分类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有些分类只是权宜之计。有些图书因其内容的复杂和交叉,既可以放在此类,也未尝不可以放在彼类。譬如《宋史·艺文志》将《山海经》放在五行类,却把郭璞的《山海经赞》放到地理类,就没有什么道理。从出土文献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一些与“兵”有关的数术占测内容,如果按《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就既可以放到兵书略的兵阴阳类,也可以放到数术略的天文类。所以对待《山海经》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分类,既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过于拘执,更不宜用后世的图书分类和对图书的认识来遮蔽其历史上的分类,从而武断地定于一尊。
关于《山海经》的主要内容,以往学术界有“人文地理志说”“神话渊府说”“博物志说”“图腾志说”“综合志书说”“史书说”“最早的小说说”“取自九鼎图像说”“巫术说”“百科全书说”等,不一而足。这些总结和归纳各有道理,但都属于以偏概全,不能囊括全体。如果用传世典籍的内容来加以比照,如《山经》部分在谈到每座山时,先是谈山的道里、名称、河流的走向和物产(包括自然物和神怪),这类似于《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接下来说物产的特点、物产的功用和物产出现预示的吉凶,这类似于《汉书·五行志》《宋书·符瑞志》和《齐书·祥瑞志》。最后有些还会涉及祭山的仪式和祭品的种类,这又可与《史记·封禅书》比照。《海经》和《荒经》部分有些地方谈到远方异国和异物,又与《逸周书·王会》《穆天子传》《博物志》和《十洲记》接近。由此可见《山海经》整体内容庞杂,性质非一,很难在已知典籍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例子给予定性。
从与出土文献的比较看,《山海经》有三个特点值得重视:
一是比较浓厚的“数术”色彩。如《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在谈到神怪时,常常会说某某神怪“见(读为‘现’)则如何如何”,如“见则其县多放士”“见则郡县大水”“见则县有大繇”“见则天下安宁”“见则天下大旱”“见则有兵”“见则天下大穰”“见则其邑有讹火”“见则天下大风”“见则其邑有恐”“见则螽蝗为败”“见则其国多土功”“见则其国多疫”“见则风雨为败”“见则天下和”等,这是战国秦汉时期数术类文献用于占测吉凶的格式化语言,体现的是将某类自然物、天象和神怪的出现与吉凶占测相对应的思想和观念。这一思想和观念影响深远,历代的志怪小说和史书中的《五行志》《符瑞志》《祥瑞志》中都有很多相同或类似内容。在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有“出所邦有丧”“出所之邦有兵”“□出,小邦有兵,得柄者胜”“此出所之邦利,以兴兵,大胜”“两月并出,有邦亡”“赤虹冬出,冬雷,不利人主。白虹出,邦君死之”“霓虹出,下有流血”“天觉出,天下起兵而无成,十岁乃已”“白灌见五日,邦有反者”“赤日、黑日偕出,大盗得”“赤日出,岁熟”“日出,赤云完之,岁饥”“黑日出,兴兵,大水,不战”“夜半见如布缄天,有邦亡”“奔星出,天下兴兵”“彗星出,短,饥;长,为兵”“彗星出所,其邦亡”等文句。文中或言“出”,或言“见(现)”,而“出”和“见(现)”意思相同,与上引《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见则如何如何”的内容表达十分接近,区别只是《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见(现)”的主角是神怪,而马王堆汉墓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出”或“见(现)”的主角是“星宿云气”等不同的天象而已。从这一点看,《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列在数术类,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是丰富的“博物学”内容。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文句对照比较密和的例子中,包括安徽阜阳汉简中的《万物》。《万物》的命名是因其文中有“天下之道不可不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W001)之句,故取其中的“万物”两字命名。《万物》有“杀鱼者以芒草也”(W057),《山海经·中山经》有“有木焉,其状如棠而赤叶,名曰芒草,可以毒鱼”,二者文义十分接近。《万物》有“卤土之已睡也”(W041),《山海经·中山经》有“来需之水出于其阳,而西流注于伊水,其中多鯩鱼,黑文,其状如鲋,食者不睡”。《万物》有“马胭潜居水中使人不溺死也”(W004),《山海经·西山经》有“昆仑之丘……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御水,食之使人不溺”。《万物》有“雏鸟之解惑也”(W012),《山海经·南山经》有“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山海经·西山经》有“其草多条,其状如葵,而赤华黄实,如婴儿舌,食之使人不惑”。《万物》有“……菽可已瘘”(W024)。《山海经·中山经》有“合水出于其阴,而北流注于洛,多

鱼,状如鳜,居逵,苍文赤尾,食者不痈,可以为瘘”。“为瘘”即“治瘘”之意。《万物》有“可以已痤也”(W013),《山海经·中山经》有“又东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婴,其状如龙骨,可以已痤”。《万物》有“鱼与黄土之已痔也”(W018),《山海经·西山经》有“有鸟焉,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名曰栎,食之已痔”;《山海经·南山经》有“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万物》有“姜叶使人忍寒也”(W031),《山海经·中山经》有“又东三十五里曰敏山。上有木焉,其状如荆,白华而赤实,名曰葪柏,服者不寒”。《万物》有“石鼠矢已心痛也”(W007),《山海经·西山经》有“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以上所引《万物》和《山海经》中记载诸物功效的用语十分接近或类似,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两者的文本性质相近。
中国古代有“万物皆可入药”的观念,因此“博物学”与“本草学”又密切相关。《万物》文中虽然有很多可入药的物品的记载,但是与后世医书中的方剂内容区别还是比较明显,尤其像“兔白可为裘也”(W009)“蜘蛛令人疾行也”(W030)和“紴缴以骨,鸟虽高,射之必及也”(W049)等文字,更是明显溢出“本草学”的领域,应该属于“博物学”的范畴。
中国古代《博物志》一类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类:(1)山川地理;(2)奇珍异兽;(3)神话传说;(4)神仙人物;(5)数术方技。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山海经》,倒是非常符合。只不过《山海经》是以地理为框架而已。从这一点来说,把《山海经》定性为“博物志说”,也是有理有据。
三是继承了“志怪”的传统。中国古代历来有“记异”和“志怪”的习惯,从甲骨文记录狩猎时俘获珍异动物的记载,到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形象和《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所云“铸鼎象物”;从《楚辞·天问》反映出的楚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上图绘的天地山川中的神灵和怪物,到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诘咎》篇;从《山海经》郭璞注提到的《畏兽画》,到梁代开始著录的《白泽图》和敦煌的《白泽精怪图》,这一传统绵延不绝。古人描摹图绘各种神怪,正如《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所说,是为了“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而“知神奸”的方法,首先就是要记住“神奸”的形象和名字,即《抱朴子·登涉》所谓“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矣”和同书《祛惑》所言“尽知其名,则天下恶鬼恶兽,不敢犯人也”。为何知道名字,就不能为害了呢?这是因为古人有一种观念,认为名字并不是约定俗成的,而就相当于其所指代的人或物。所以知道了人或物的名字,也就相当于知道了祛除的方法。睡虎地秦简《诘咎》篇记载了很多鬼的名字和驱鬼的方法,可以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其内容与《山海经》的《山经》部分中谈神怪的内容很接近。尤其是《山海经》谈到对待神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食之”,这与睡虎地秦简《诘咎》篇谈到对待某些鬼的方法是“烰而食之”(简四九背壹)、“烹而食之,美气”(简三七背贰—简三八背贰)、“烹而食之,不害矣”(简六六背贰)如出一辙。《白泽图》或《白泽精怪图》的“白泽”是神名,源自《云笈七签》:“帝巡狩东至海,登桓山,于海滨得白泽神兽,能言,达于万物之情。因问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者,凡万一千五百二十种,白泽言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抱朴子·极言》:“穷神奸则记白泽之辞。”同书《登涉》:“其次则论百鬼录,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在《白泽图》或《白泽精怪图》流行的时代,很多人家都藏有《白泽图》或《白泽精怪图》,或是悬挂在墙,或是张贴在门,都是为了随时对照翻查鬼怪的形象、名字以及祛除方法。《五灯会元》:“师曰:‘家有白泽之图,必无如是妖怪。’”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谈到《山海经》的文本形式,主要是指《山海经》的附图问题。关于《山海经》附图的讨论,一直是《山海经》研究的一个重点。确定《山海经》有图,是从郭璞的《山海经图赞》开始的。唐宋之后各种《山海经图》日渐增多,但都逐渐佚失,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都是明清之后的图。现在的问题是:郭璞《山海经图赞》参照的图,是《山海经》原初的图,还是郭璞或郭璞同时代其他人配的图,至今尚没有明确证据;还有最初的《山海经》图,是和如今看到的图一样,仅仅画有各种神怪,还是除神怪之外,还包括山川地理形貌等地图,目前也说不清楚。从《山海经》的内容,参照出土文献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山海经》很可能最初就配有图,是比较早的“图书”。因为从出土文献看,战国秦汉时期有关数术类的著作,大都配有附图。比较典型的如长沙楚帛书,四周画有代表“四时”的“神木”和四边每边三个共十二个代表十二个月的“神怪”。秦简中与数术有关的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艮山图》(《艮山图》又见于周家寨汉简和孔家坡汉简)、《人字图》(《人字图》又见于周家寨汉简、马王堆帛书《胎产书》、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孔家坡汉简和北大藏汉简)和《置室门图》,《日书》甲、乙种又都有《死失图》,马王堆帛书中有《禹藏埋胞图》《堪舆图》《刑德小游图》《传胜图》《地刚图》《木人占图》《卦象图》《物则有形图》《九主图》等,银雀山汉简有《九宫图》、尹湾汉简有《六博图》。其中形式上与《山海经》附图最为近似的就是长沙楚帛书上的图和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图。长沙楚帛书文字部分的内容包括伏羲女娲神话,周边有十二个神怪的图像,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文字内容是讲天象预示的军事吉凶,并附有各种天象的图像。长沙楚帛书从文字内容到附图形式,都与《山海经》部分内容和所附之图非常接近;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的内容虽然涉及的是天文和兵阴阳,这一点与《山海经》不同,但是其以不同天象的出现预示军事吉凶并附图的形式,与《山海经》以不同的神怪出现预示吉凶并附图的形式完全相同。
出土文献中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附图跟记录文字的载体有关。以竹木简为记录载体的数术类著作中所附之图,大都是一些表示方位、干支等表格类的图,像《人字图》那样画有人形且比较写实的图则偏少。但是在以缣帛为记录载体的数术类文本中,却有很多星宿、云气和神怪等更为写实形象的图,如长沙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这是因为竹木简每支宽度有限,简与简之间存在空隙,因此画复杂写实的图受限制,而帛书则不受这个制约,画图更为自由,因此缣帛上才会有更多复杂写实的图。所以从图文搭配的形式看,帛书才是当时“图书”的代表。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山海经》是一部带图的综合性图书,如果一定要给《山海经》的文本性质作一个定性的话,大可不必用已有的传世典籍来套,而是应该给出一个稍显宽泛的称呼,譬如称之为:在地理框架下杂糅着数术、博物、志怪和神话等内容的综合性图书。这样命名似乎才更为接近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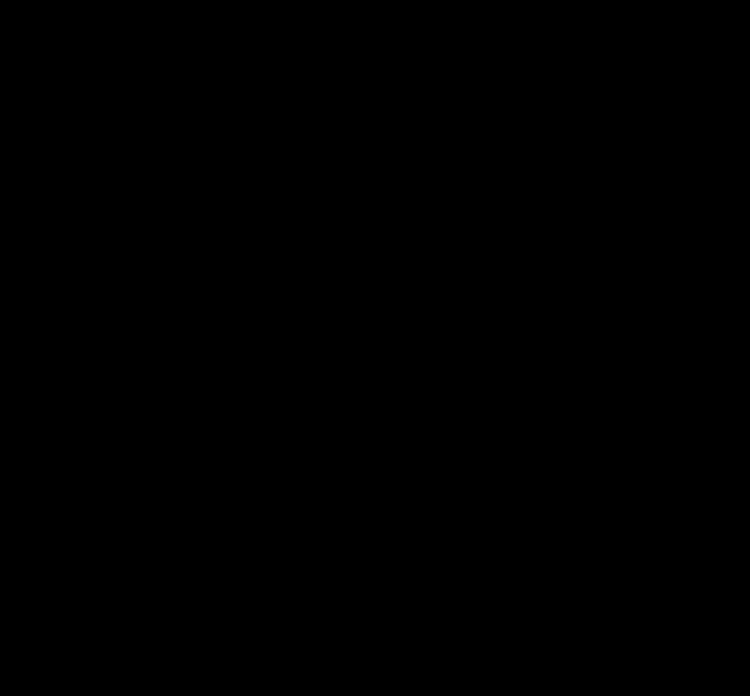
二、《山海经》的史料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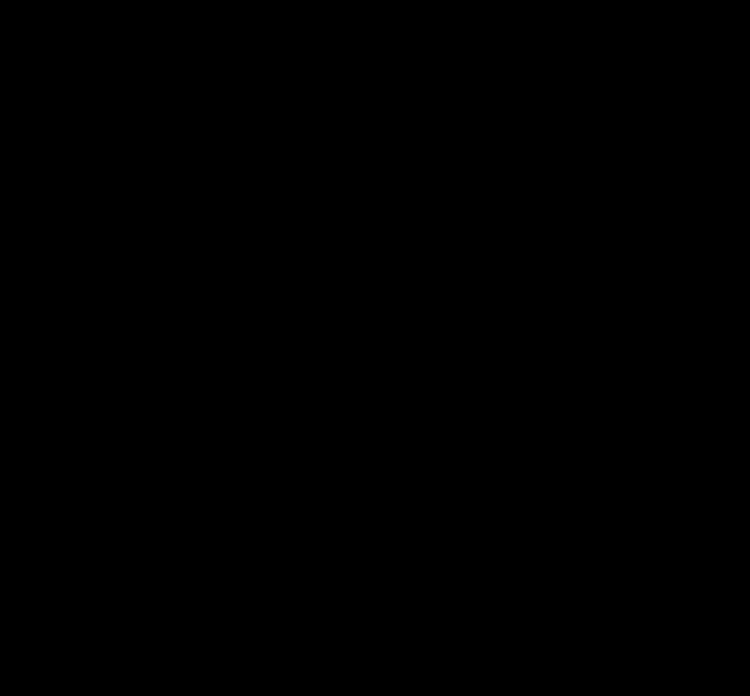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列《山海经》于史部古史类,已经认为《山海经》中有可信之史料,可谓颇有识见。王国维更是很早就指出:“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楚辞·天问》,成于后世之书如《晏子春秋》《墨子》《吕氏春秋》,晚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然则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王国维对《山海经》作出这样的判断,缘于他对出土资料的熟悉和感悟。他发现甲骨文中记录商代先王“王亥”的“亥”字经常写成上边有一只鸟的形状,与《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中王亥“两手操鸟”的记载可以互证。20世纪40年代初胡厚宣先生发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紧接着又与丁声树先生合作写出《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补证》,之后又加以修订写成《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到50年代初再加入新的缀合资料写成《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一文。该文发现甲骨文中的四方风名与《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四方风名有很多相合之处,这与《尚书·尧典》中的一些记载也有关联,既可以订正《山海经》的一些错误,又可以说明有关四方风的思想和观念起源很早。以上所列王国维和胡厚宣两位的发明发现,揭示了《山海经》蕴含的神话史料可与出土文献互证的事实,说明《山海经》“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所以“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可以说是利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山海经》的典型范例。
近些年公布的出土文献可以补充如下一些与《山海经》互证的例子:
其一,安徽大学藏楚简中有《楚纪》篇,记录了楚国从早到晚的历史,非常详细。其中提到楚国先祖“穴熊”和“老童”的起名缘由。如说到“穴熊”时说:“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酓(熊)。’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酓(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熊),是为荆王。”可见“穴熊”一名的来由,是因为酓(熊)生活在山洞或地下穴道的原因。而据简文记载,“老童”的得名是因为“老童”生下来时就满头白发,状如老人,因此命名为“老童”。这都是以往不知道的新知。《山海经·中山经》:“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萧兵说:“在以熊称的楚王名字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那较古老的‘穴熊’——这分明说出自熊穴,或穴处的熊祖。”并据上引《山海经·中山经》的记载推测说:“这熊穴自是巨熊蛰居或冬眠之所。熊穴神人莫非暗指楚祖穴熊?”萧兵这一推测以往不被重视,如今看来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也凸显出《山海经·中山经》这条记载的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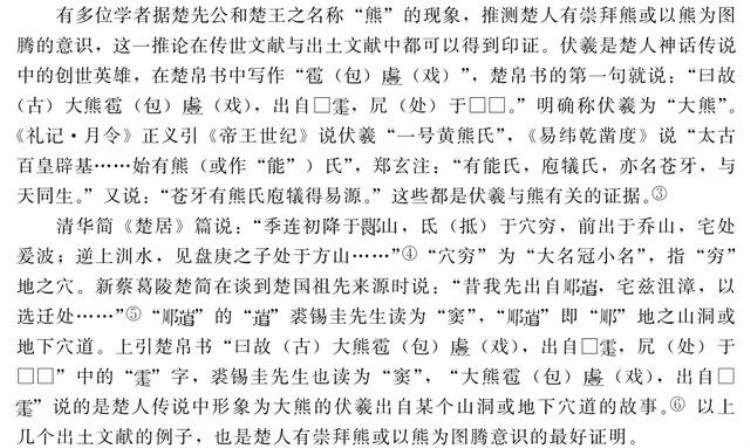
其二,北京大学藏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中,有一段在讲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和贤臣的发明创作之功时说:“始诸黄帝、颛顼、尧、舜之智,循鲧、禹、皋陶、羿、

之巧,以作命天下之法,以立钟之副,副黄钟以为十二律,以印久天下为十二时,命曰十二字,生五音、十日、廿八日宿。”文中提到的帝王和贤臣中,黄帝、颛顼、尧、舜、鲧、禹、皋陶、羿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唯独“

”似乎未曾听闻。原整理者解释“

”字说:“

‘’字下部作‘番’,疑为‘垂’之讹,‘箠’应读为‘垂’,亦作‘倕’,古书引《世本》有‘倕作规矩准绳’、‘垂作耒耨’、‘垂作耜’、‘垂作钟’、‘垂作铫’等语,或曰黄帝之臣,或曰尧之巧工,或曰舜臣,说法不一。”又引《墨子·非儒下》“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为证。这一解释看上去颇有理致,其实却是有问题的。对此郭永秉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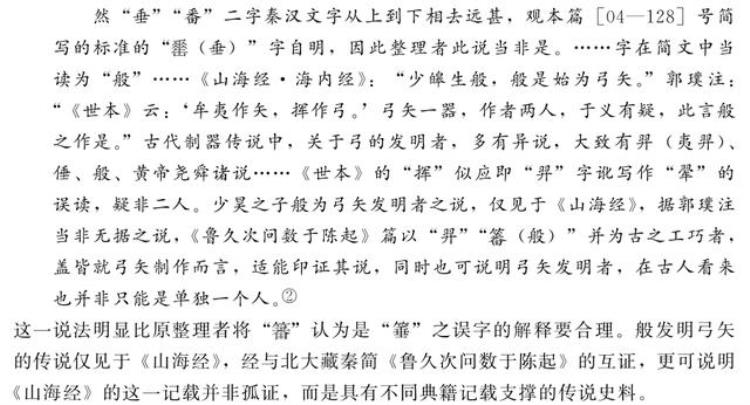
其三,《山海经·海外北经》:“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为人两手聂其耳。”郭璞注:“言耳长,行则以手摄持之也。”又《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郭璞注:“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镂画其耳,亦以放之也。”袁珂《山海经校注》案:“儋耳,《淮南子·地形篇》作‘耽耳’,《博物志》卷一作‘擔耳’,依字‘儋’当为‘聸’。《说文》十二云:‘聸,垂耳也。’即郭注所谓‘耳大下儋,垂在肩上’之意也。”《抱朴子·杂应》提到老子形象时说:“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老子名耳,字聃,从古人名字相应的规律看,“聃”字的含义一定跟“耳朵”有关。“聃”字与“儋”“耽”“擔”“聸”诸字皆音近可通,寓意都是指耳朵长,所以从老子的名字来看,显然就来自其“耳长七寸”的特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有周太史儋,历来研究者或认为与老子就是同一人,或认为另有其人,无论如何,这个周太史儋的名字“儋”,很可能与老子的名字取意相同。春秋时期的晋文公名重耳,后世典籍记载其有异象,即“骈肋重瞳”,于是有人猜测其本名“重目”,后改为或误为“重耳”,或说“重耳”是指耳垂双重。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证据的猜测。“重耳”的“重”虽然《经典释文》记其音读为“重复”之“重”,但《经典释文》时代偏晚,其记录的读音不见得是早期正确的读法,“重耳”的“重”完全可能读为“轻重”之“重”。“耳长”必然会沉重,所以如《山海经》才会说“两手聂其耳”。陆德明《老子道德经》释文云:“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河上公注把老子之名与晋文公重耳之名加以等同,虽然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但也可能说明当时有人就认为晋文公重耳之名就是指“耳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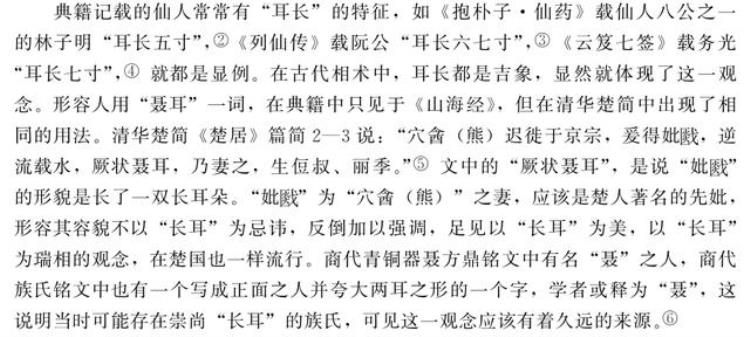
以上所举出土文献证明《山海经》史料价值的资料,都是有关神话或传说的内容。这些有关神话或传说的史料既揭示了《山海经》的性质,同时也印证了王国维所说:“虽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这些神话或传说史料一样能够描绘古代中国的精神世界的图景,并从中窥探古人的思想观念,从而证明或解释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以也绝对不能轻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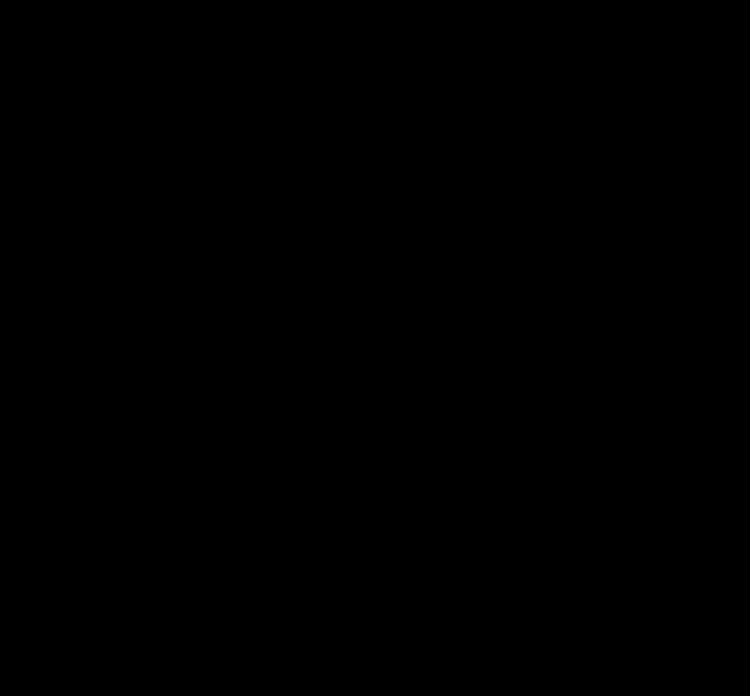
三、《山海经》的产生时地与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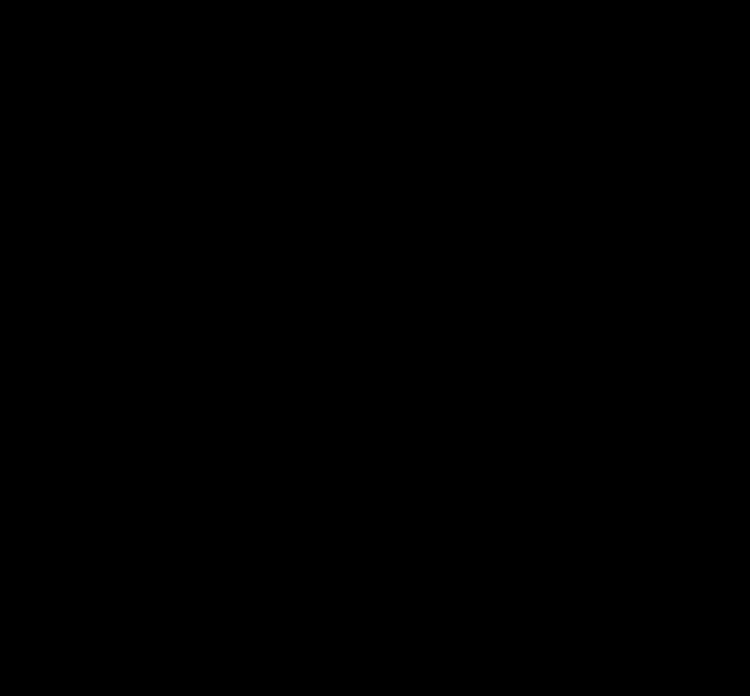
关于《山海经》产生的时地与作者,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陆侃如认为《山经》是战国楚人所作,《海内经》和《海外经》是汉代所作,《大荒经》和《海内经》为东汉魏晋所作;茅盾认为《五藏山经》是春秋时作,海内外经至迟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荒经》的成书也不会晚于秦统一;蒙文通认为《荒经》以下五篇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经》四篇较迟,但也在西周中叶。《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最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作品。《海内经》是古蜀国人所作,《大荒经》是巴国人所作;袁珂认为《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成书最早,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稍迟,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海内经》四篇最迟,成于汉代初年。他们的作者都是楚人——即楚国或是楚地之人。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山海经》的作者应该是秦人,也有的研究认为是齐人或燕人。
前文说过,《山海经》内容庞杂,其内部差异也很大,很可能并非一时一地所作,所以谈论《山海经》的时地和作者,只能就一部分立言,不能全书一概而论,因此本文只想就《山经》部分的时地和作者作些推测。
探索一部文本的产生时地和作者,全面考察文本的用字用词习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就是通过《列子》在用字用词上的某些特殊现象和魏晋时期的一些新词新义,判定《列子》应出自晋人之手。这是利用词汇史的观点推定文本产生时代的一篇经典范文。本文也试图利用这一方法,从出土文献与《山海经》用字用词习惯对照的角度,推定《山海经》的《山经》部分的产生时地和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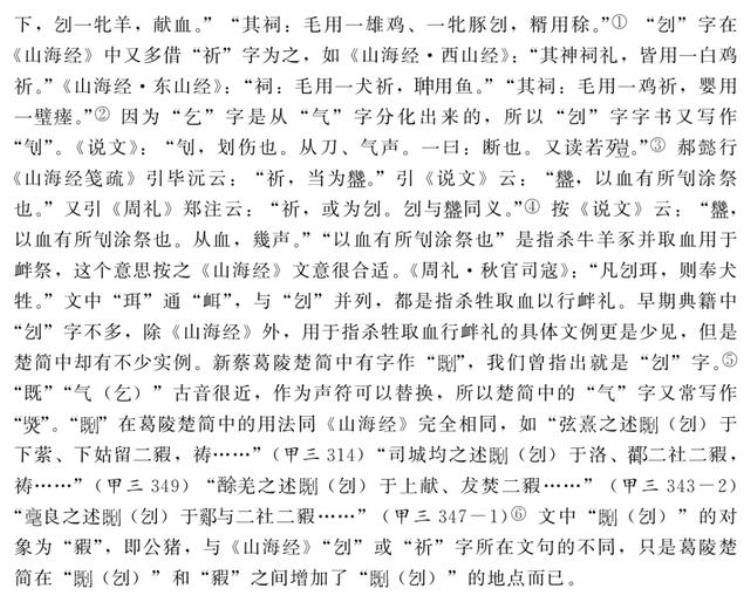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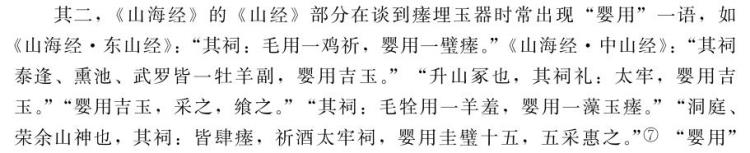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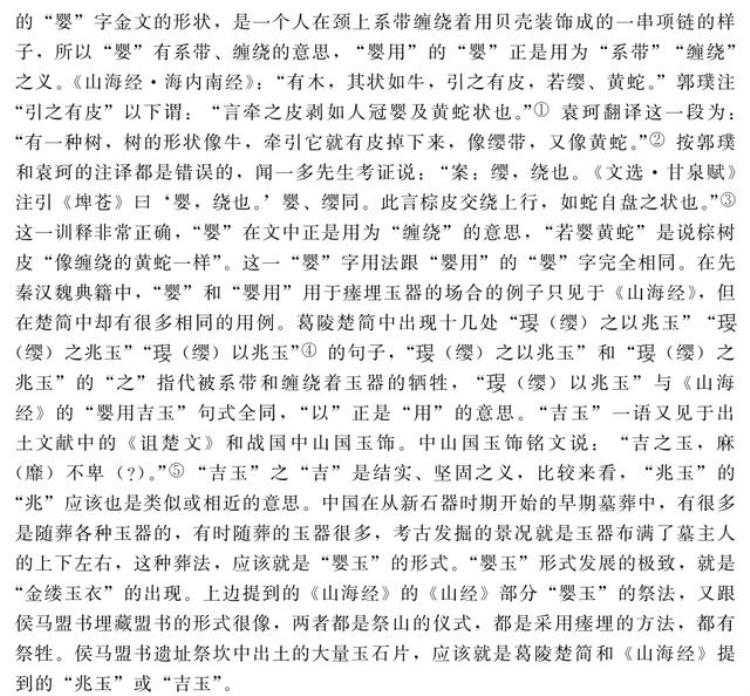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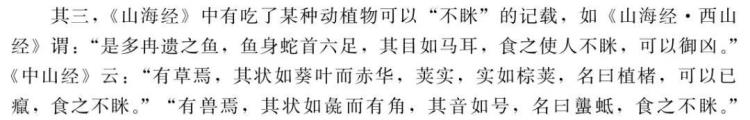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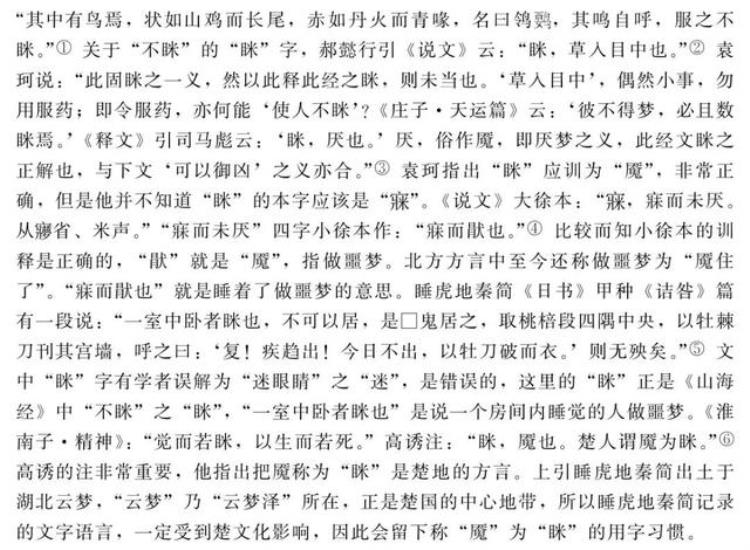
其四,《山海经·西山经》说:“(皋涂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郭璞注:“今礜石杀鼠,音豫;蚕食之而肥。”“礜”是一种性热含毒的矿石,即硫砒铁矿,也叫毒砂,是制造砒霜的主要原料,可以用之炼丹,中医又常用之入药,为“五毒之药”之一,其功用是祛除“邪祟鬼疰”,魏晋时期还被作为“五石散(又称寒食散)”的主要成分。因礜石色白,故又称为“白礜”或“白石”。《抱朴子·登涉》:“山中见吏,若但闻声不见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掷之则息矣。”以往各种训释都将“白石”误解为“白色的石头”,其实这里的“白石”就是指“礜石”。因为礜石可以祛除“邪祟鬼疰”,所以可以用来驱鬼。用“礜石”驱鬼的实例还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咎》篇,简文说:“鬼恒召人之宫,是是遽鬼毋所居,罔謼其召,以白石投之,则止矣。”(简二八背叁)句中的“以白石投之”与上引《抱朴子·登涉》的“以白石掷之”非常接近,可以类比。简文中的“白石”以往也被误解为一般的“白色石头”,这也是错误的。汉印中有“左礜桃支”印,疑为道家驱鬼之印,印文中的“礜”和“桃支(枝)”都是驱鬼之物。“左”为“东”,代表阳,“鬼”为“阴”,故桃树朝东的枝条更适用于驱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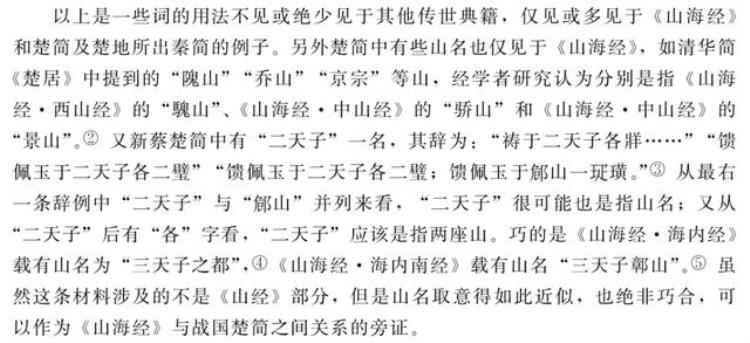
以上例证似乎都表明《山海经》的《山经》部分的产生时地,与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地或秦时的楚地有关。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因目前所出的战国简基本都是楚简,因此将《山海经》之《山经》部分的产生时地与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地或秦时的楚地相联系,是不是有使用“默证”之嫌?其实除了以上揭示的《山海经》与楚简在用词上的近似之外,还有两者用字习惯上的相同,这一点将在下一节加以论述。此外,楚帛书上的神怪形象,以往的研究皆将其与《山海经》附图上的神怪相对照,找出了很多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如楚帛书中有三头人神怪,在《山海经·海内西经》有“三头人”,《海外南经》:“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一身三首。”“一身三首”的形象与楚帛书上的“三头人”完全一致。还如《山海经》中有很多神怪“操蛇”“衔蛇”“戴蛇”“珥蛇”的记载,而在楚帛书上的神怪中,就有两个衔蛇的形象和一个操蛇的形象。在楚地出土并呈现出鲜明的楚文化风格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漆棺上,也有“衔蛇”和“操蛇”的神怪形象,这似乎都表明神怪“操蛇”“衔蛇”“戴蛇”“珥蛇”,是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以上诸种例证,都在《山海经》与楚国或楚地之间建立起了关联,所以这一节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山海经》的《山经》部分的产生时代至迟不晚于战国,产生的地域很可能是在楚地,其作者也应该是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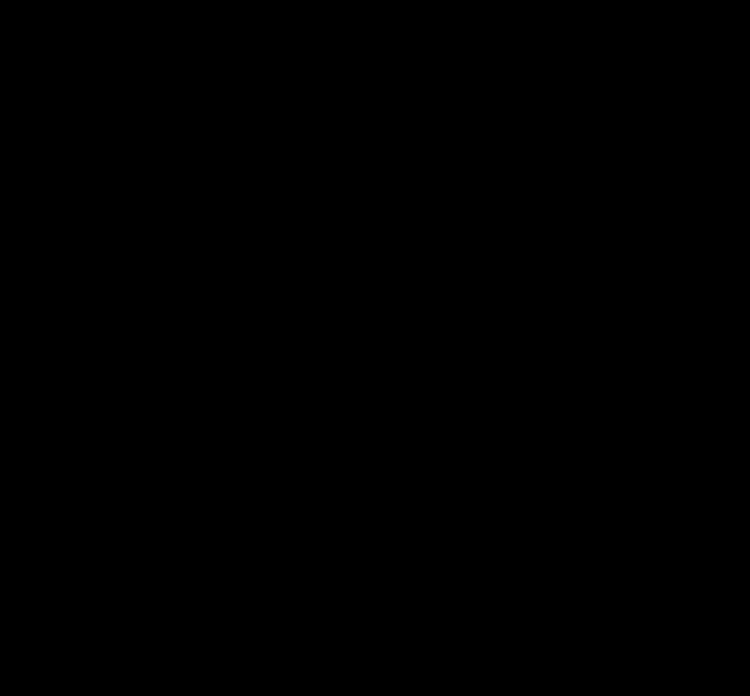
四、《山海经》的文本文字校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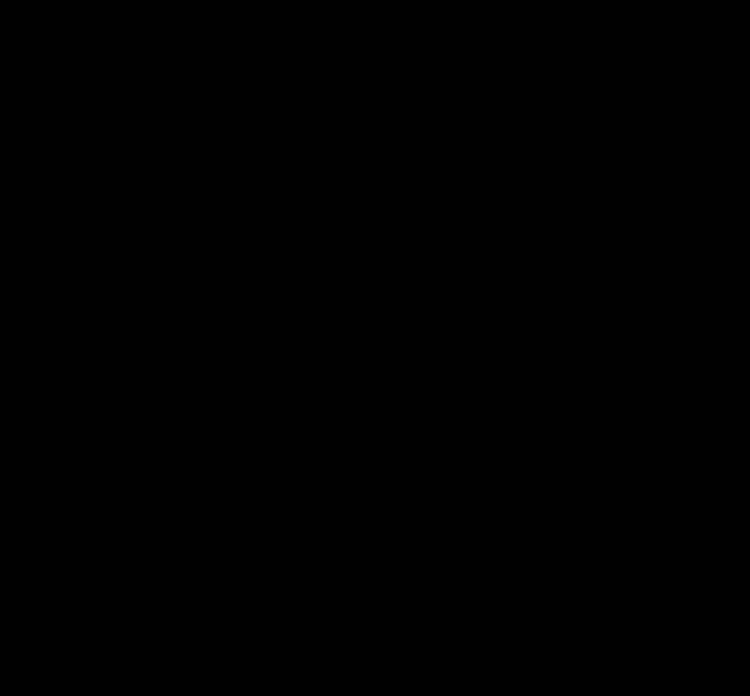
从《山海经》郭璞注开始,历代都有相关著作或多或少涉及《山海经》文本文字校释问题,但是成绩不大,不足为观。直到清代的毕沅和郝懿行,才有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意见。随着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从古文字角度审视《山海经》的文本,也会有一些发现,下边试举例证之。
以往学术界曾有一些成功的校释之例,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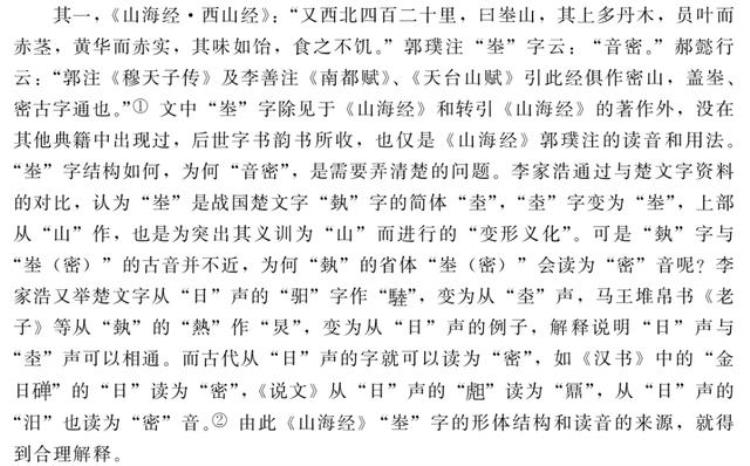
其二,《山海经》的《山经》部分在说到祠山时的用牲法时,常常出现“毛”字,如《山海经·南山经》:“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西山经》:“其祠之,毛用少牢,白菅为席。其十辈神者,其祠之,毛一雄鸡,钤而不糈;毛采。”《北山经》:“其祠之,毛用一雄鸡彘瘗,吉玉用一圭,瘗而不糈。”“其祠:毛用一雄鸡彘瘗。”《东山经》:“祠:毛用一犬祈,

用鱼。”“其祠:毛用一鸡祈,婴用一璧瘗。”《中山经》:“其余十三山者,毛用一羊,县婴用桑封,瘗而不糈。”“其祠之,毛用一白鸡,祈而不糈,以采衣之。”“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稌。”“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刉,糈用稌。”对于上引文中的“毛”字,郭璞注谓:“言择牲取其毛色也。”袁珂说:“毛谓祀神所用毛物也,猪鸡犬羊等均属之。此言‘毛用一璋玉瘗’者,以祀神毛物与璋玉同瘗也。郭注不确,诸家亦竟无释。”从文意看,郭注和袁珂的解释都不可信。《山海经》在用“毛”字的语法位置上,有时却用“皆”字,如《西山经》说:“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这说明“毛”也可能用为总括之词,为“皆”“都”“全”之义。正好在出土的楚文字里有很多用法相同的“屯”字,如信阳楚简中有:“四方鉴,四团□,二圆鉴,屯青黄之瑑。”(2-01)“二方鉴,屯雕里。”(2-09)“七见鬼之衣,屯有裳。”(2-13)“一汲瓶,一沐缶,一汤鼎,屯有盖。”(2-14)在其他类楚文字里也有相同之例,如:“二戟,屯三戈,屯一翼之曾。”(曾侯乙墓竹简)“屯三舟为一舿”(鄂君启舟节),“如马、如牛、如儓,屯十以当一车;如担徒,屯二十担以当一车。”(鄂君启车节)战国文字中“屯”字和“毛”字的形体很接近,极易讹混。以上证据皆表明,上引《山海经》中用为总括之词的“毛”字,都应该是“屯”字的讹误,这些“屯”字在文中就用为“总括之词”。
以下是笔者新考释的几个例子:
其三,《山海经·中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養之可以已忧。”按《山海经》中讲到神怪时,说“養之”仅此一见,似与全书说解内容和习惯不合。《山海经·北山经》说:“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可以已忧。”又《西山经》谓:“有草焉,名曰薲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袁珂说:“已劳,谓已忧也。”从理校角度分析,可知“養之可以已忧”之“養”应为“食”字之讹。秦汉时期写得比较草的“養”字,上边已经写得很简略,很容易误为“食”字,所以“食之可以已忧”错成了“養之可以已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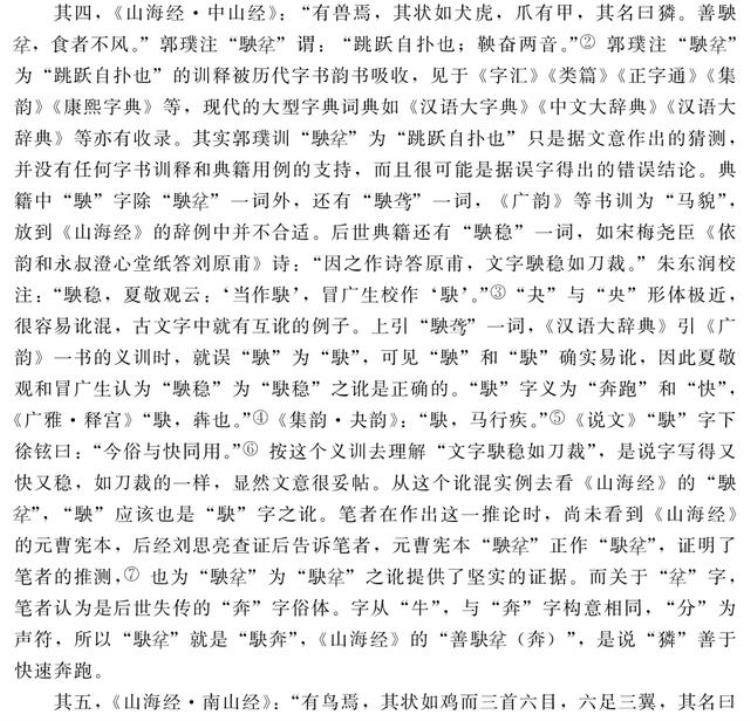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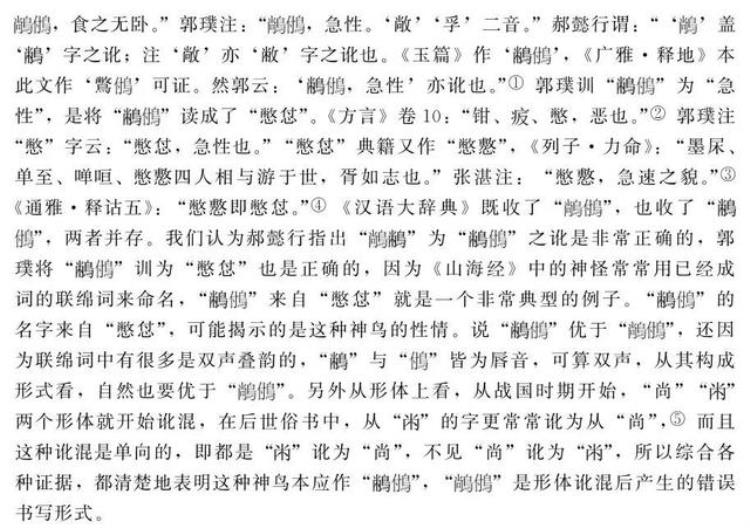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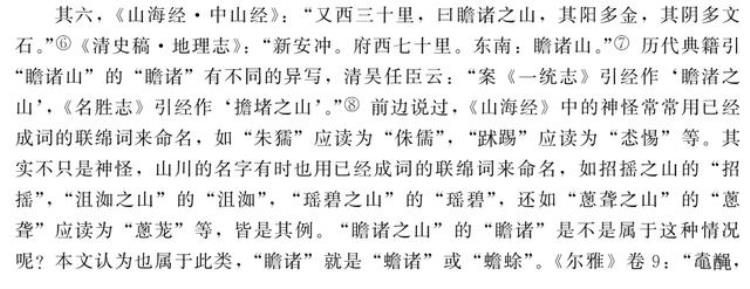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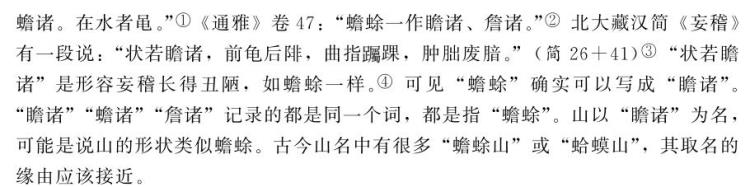
以上本文从几个方面,以举例对照的形式,用出土文献和古文字资料对《山海经》进行了一些阐释和新证。这一工作目前还是初步的,随着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资料的不断面世,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新资料可以不断给我们带来新见新知,将其与《山海经》进行对照并加以阐释和新证,进一步抉发出土文献和蕴含在《山海经》中的史料和语料,推进《山海经》的新证工作和《山海经》文本的深度整理。

《山海经》的作者是谁?为何他能写下这样一本奇书?
《山海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老”到什么时候?至少写于公元前两三百年,甚至更早。
司马迁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开始写《史记》。当时他已经看了《山海经》。而且,他没有潦草地穿过它,他一定是认真地读过它。不然《史记》他也不会具体说。他为什么不把《山海经》的账号写成《史记》?这说明《山海经》在当时是一本有影响的书。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说‘昆仑昆仑流出的河流有2500英里高,太阳和月亮像光一样相互避开。上面有礼泉和华钥池。今天,自从张骞造了夏天,河源就穷了,而那些讨厌看到所谓的昆仑的人在这个世纪呢?因此,《尚书》接近九州的山川水水对《禹本纪》 《山海经》一切妖魔鬼怪,余不敢说话。“——”翻译成白话文是:《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海拔2500米的昆仑,山余,是太阳和月亮互相遮挡,发出各自光芒的地方。昆仑上方有礼泉和瑶池”张骞出使到夏季后,终于找到了黄河的源头在哪里可以看到《禹本纪》中提到的昆仑山?所以当谈到九州,的山川时,《尚书》说的最接近真实情况。至于《禹本纪》和《山海经》记载的妖怪,我不敢说。
这也说明司马迁写的《史记》,对它所依据的材料是非常客观严谨的。另外,他没有提到《山海经》的作者。
《山海经》是一个原创神话故事,而这个时期恰恰是很多基于《山海经》的奇幻小说故事的时期,比如《搜神记》,也是网络流行语“野性的力量”。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山海经》成为了很多建筑世界观的原型和蓝图。
《山海经》描述了很多古代的世界,比如原信封的“图腾”文化,如下图:“我是少昊,高祖,我是好鸟,所以我属于鸟,鸟名为鸟师”。它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原始观点,如夸父化身为山川邓林。就像地球上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一样,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动物了。《山海经》中有很多对古代动物的描述,甚至还有人、动物等动物。同时《山海经》也反映了很多古人的精神生活,比如和谐共处,描述了多少动植物和人类在一定范围内和谐生长。同时,很多童话都体现了人类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比如精卫填海,天天夸父等等。很多故事都有很强的悲剧意识,审美价值和伦理道德,有生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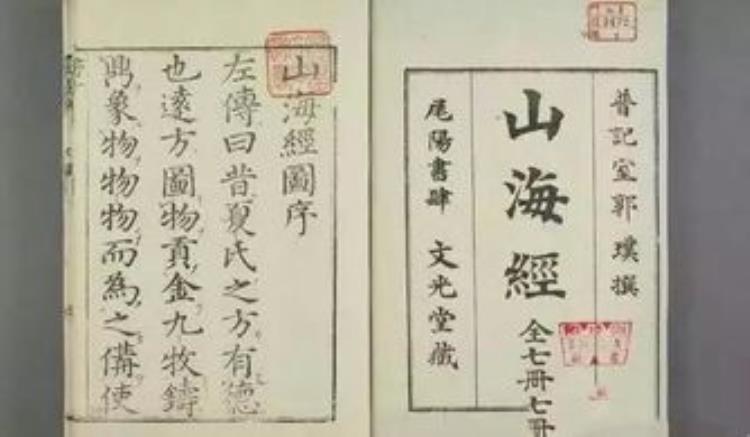
(转载)美国学者实地步行验证【山海经】所言真实不虚!
《山海经》与美洲一我最早知道《山海经》与美洲有关系一事,是在连云山所着《谁先到达美洲》一书中,读到一则介绍:美国学者墨兹博士研究了《山海经》,根据经上所说《东山经》在中国大海之东日出之处,他在北美,试着进行按经考察,经过几次失败,他一英里一英里地依经上记过的山系走向,河流所出和流向,山与山间的距离考察,结果胜利了。查验出美国中部和西部的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喀斯喀特山脉,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与《东山经》记载的四条山系走向、山峰、河流走向、动植物、山与山的距离完全吻合…… 真是令人惊讶:一个美国人,研究了中国学者都难以读通的《山海经》,并且据此实地勘察,发现了中国古人早已到达美洲!这件事的确让我着迷。后业,我又读到贾兰坡老先生为这个美国博士的着作《淡淡的墨痕》(《PALEINK》,中文译着名为《几近退色的记录》)所撰写的序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位凭借双脚踏勘美洲几列山脉的美国学者竟然是位令人尊敬的女士。或许是不同译者的译名,使连云山先生将亨利艾特·墨兹误认为男性;或许是觉得独自一人冒险走遍四列山脉的人不可能是一位女子。有的译者将这位女博士的名字(HenriettaMertz)译为亨丽艾特·茉芝,这样,中国读者一看便知是位女性。而《人民日报》驻海外记者袁先禄在一篇题为《墨淡情浓》的访问记中,将被访者的名字译为:亨丽埃特·墨茨。据我所知,袁先禄先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访问默茨博士的资深记者。遗憾的是,当我辗转寻访到袁先禄先生的夫人姚堤女士时,方才得知袁先生已然病故;而默茨博士呢,在袁先禄八十年代初访问她时,已经八十多岁,如今二十年过去,想来她已不在人世,令人黯然。好在袁先禄先生留给我们一篇《墨淡情浓》①,读了这篇访问记,我们好象跟随着袁先生一起,在风和日丽的芝加哥东南湖滨造访了默茨女士。还有她留下来的那本浸透她心血的着作。在这本书的原着序里,默茨博士回忆道,她是最先受到维宁(EdwardVining)有关着作的影响,并仔细研读了维宁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于是,“《山海经》里的这些章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着手对证古本,一里又一里地循踪查对并绘出地图……”
真是令人汗颜!一部中国上古流传至今的宝贵典籍,却是由一些欧美学者用尽心力地在进行着再发现。
《山海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地理历史着作。清代毕沅考证其“作于禹益,述于周秦,行于汉,明于晋”。然而由于其成书年代过早,且奇闻怪事、神怪传说等夹杂,难于考证,故而二千多年来,一直有怀疑者认为该书“闳诞迂夸,奇怪 傥”,连司马迁也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清代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干脆将《山海经》归于志怪小说一类。鲁迅也因该书记载了很多巫师祀神的宗教活动,而认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而疑古大师顾颉刚则更予以全盘否定。当然也有如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校订该书时,给汉成帝上表,力陈《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着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近年来学界对《山海经》的呼声日高。有的学者研判《山海经》,认为书中有关种种山神乃“鸟首人身”、“羊身人面”、“龙首鸟身”、“龙身马首”、“人面蛇身”等等,其实是原始初民的图腾神像和复合图腾神像,源于先民特有的图腾崇拜。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至于巫师的祀神活动,是上古部落族日常必有的宗教活动。巫字本意就是指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是代替人们承接天意的人,故而原始初民社会,部落酋长往往兼具巫师职责,率领万民祀神。
至于《山海经》中记载的大量神话,也绝不能以貌似怪诞而简单地贴上神话标签,不重视其所传述的历史内涵。其实原始初民正是通过神话传说,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记录下来。《孔子集语·子贡第二》引《尸子下》,讲了一则孔夫子解读神话的故事。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过去,传说黄帝有四个面孔,你信吗?孔子回答,这是黄帝任用了四个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去治理四方,他们彼此不用协商就和谐一致,这就叫四面,并非黄帝真有四个面孔。这似乎为我们解读《山海经》中的神话提供了一种方法。
倒是美国学者默茨直截了当地指出《山海经》中大量的有如旅行记录般的客观记载:“谁如果仅仅念上几句这样的‘神话’,就会清楚地感到写这些话的人是诚恳的……一里又一里,里程分明的记录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梦想,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幻境。扎扎实实的、客观的事实是:‘过流沙往南100英里,曰秃山,大河东流。”②这里没有什么奇想。
于是,在反复研读推证后,默茨背起行囊上路了。她要像中国古代的旅行者一样,用双脚去丈量勘测那些山脉。她的方法是:《山海经》中的中国古人让你向东,你就向东,让你走三百里,你就走三百里,看看会发现什么。
这位思维完全是开放型的美国女性又带给中国学者一个困窘。她写道:“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学者们在全国寻找线索而一无所获,于是只好作罢……”
就目前所见资料看,中国人研究《山海经》还只是考证史料,查找地图。
人们发现,《山海经》中,《南山经》已写到浙江绍兴界:“又东五百里,曰会稽之山……”晋代郭璞注云:会稽之山,“今在会稽山阴县南,上有禹冢及井。”而会稽正是现在绍兴的古称。而《北山经》则写到了河北界的太行山和沱河:“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
“木马之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 沱。”“空桑之水出焉,东流注于 沱。”
而《东山经》中所到四条山脉多无可考,因中国东部乃冲积平原,何来四列山脉,默茨所说的中国人“开始在国内核对《山海经》所描写的某些山脉,但未能找到”,指的主要是《东山经》所列的山脉。
于是,默茨便“心安理得地越过大海”,到美洲去踏勘了。默茨历经艰难险阻,踏勘的结果是:
第一列山脉,起自今美国怀俄明州,至得克萨斯的格兰德河止,共12座山。将古华里换算为英里,与《东山经》中第一列山的距离完全相符。
第二列山脉,起于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的温尼泊,止于墨西哥的马萨特兰,共17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二列山脉相合。
第三列山脉是沿海岸山脉的太平洋沿岸,完全走太平洋海岸航行,起于阿拉斯加的怀尔沃德山,至加州的圣巴巴拉,共9座山。距离也与《东山经》所列第三条山脉相符。
第四列山脉,起于华盛顿州的雷尼尔火山,经俄勒冈州到内华达州北部,共8座山,距离与《东山经》第四列山相合。
于是默茨宣告:“过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国人认为是神话的《山海经》,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文字记录。珍藏在中国书库中的这部文献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人便已到达美洲探险,而这些材料迄今为止一向是很缺乏的。”
对于默茨的考察结果,中国学者能说什么?我们可以不相信,可以认为是“臆说”,但反驳必然无力,因为没有中国人也象默茨那样,迈开双脚丈量中国东部山水,找出《东山经》所列四条山脉到底在中国何处?
最有力的办法还是依旧给《山海经》贴上神话的标签,置于故纸堆中,不予理睬!
可叹,中国历史上,像徐霞客一样的旅行家实在太少了。一句“父母在,不远游”,羁绊了中国人的步伐,也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
二
其实剔除《山海经》由于年代久远,出现错简、残简、漏简等错生命线,其内容之可信,屡使后人称奇。
《山海经》古传有三十二篇,西汉刘向、刘秀(歆)父子最早校订此书时,定为十八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
刘秀最后校订完成《山海经》十八篇后,为此专门给皇帝上表,其内容今日可看做一篇出版内容简介:
……《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风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着《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着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
接下来,刘秀为了向皇帝说明“其事质明有信”,还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例是:
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
刘向、刘秀(歆)父子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校订《山海经》之人。他们看到过的《山海经》是“凡三十二篇”,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是经他们校订删编而定的十八篇。对于《山海经》,刘氏父子应最有发言权的。何况为此皇帝上表,是“臣秀昧死谨上”,岂敢胡言乱语?
今日事实证明,《山海经》确实“其事质明信”。现举几例,真让人称奇:
其一,在闻名于世的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个祭器坑中发现许多保存完好的象牙,而今日成都平原又不是野象栖息地;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玉器,而成都平原并不出产玉石。翻开《山海经》便可找到答案。《山海经·中次九经》指出:“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岷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白珉即是白色的硅质类岩石。这就指明了三星堆遗址中象牙和玉石器的来源。而三星堆出土的人首鸟身青铜像,也与《山海经·中次八经》中的山神形象相合。
其二,清末民初曾任清朝政府和尼国政府驻外使节的欧阳庚先生之子欧阳可亮,耋年曾跟随其父在中南美洲生活多年,相识不少印第安人,曾有一段奇特的经历,现将欧阳可亮先生的自述摘录如下:
“笔者耋年在海外,与殷地安人(欧阳可亮认为印第安人实应为殷地安人,有殷人之意)家庭同吃同住同学同游六年,1926年6月15日,与欧阳可宏三哥、可祥五弟,受殷福布族招待,派二十名殷福布族青年水手划船,从墨西哥支华华(CHIHUAHUA)州的支华华市支华华村的甘渊汤谷(即 谷)23人上船,一路上有800公里地下钟乳古水道,实入《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之大壑、甘渊、归墟、咸池,而不自知。由黑(墨)齿国(即墨池国)之尤卡坦半岛科潘河上岸,出墨池(归墟),到拉文塔太阳神庙遗址。见日出杲杲,朝阳东升于穹桑树上,殷地安群众已集数百,礼拜太阳。20名水手也站立挺身,仰面朝天祈祷。回去时,仍由大壑、咸池,进入地下钟乳水道,在墨池归墟饮‘合虚山长寿甘泉的甘露水 ,见有地下水道岔口,钟乳下垂滴水,蔚为壮观。一水手说:这岔道是天元(TIENYUEN)日月山,常羲(CHANGSI)妈妈正在浴月,一月方至,一月方出。三哥问:怎么墨国也有轩辕呢?答:这是海外天元。指又一钟乳大岔水道说:这是羲和(SIHO)妈妈浴日的地方,共有22个地下岔道,一进去,迷了路就出不来了……我们兄弟3人1927年才回中国学汉语,当时只会说西班牙和殷地安语,23人谁也没读过《山海经》,后来才知道水手讲的同《山海经》记的多有暗合,很是惊讶……
1926年这次游历终生难忘,因我童年和殷福布族等殷地安人生活,彼此互称殷地安,自言中国人,确信美洲‘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商殷人和少昊、夸父等中华先人的裔胃。③
其三,再说到默茨。默茨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读到开篇一句:“东海之外大壑”,并《海外东经》中羿射九日神话之源:“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默茨认为,“大壑”便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他们在四千年前称之为‘大壑’,我们今天称它为‘大峡谷’。人们站在大峡谷边上眺望,无不为它瑰丽的景色所感动。印第安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中国人不能,我们也不能。”默茨进而推断道:中国关于羿射日的神话,其出处无疑就在《山海经·海外东经》。“我相信终有一天会发现,射日的故事最早发源于某一印第安人的部落,是印第安人讲给中国人听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关于峡谷怎样形成的神话,作为大壑(大峡谷)的神话带回来……印第安人是想解释峡谷是怎样来的,想弄清为什么会流金铄石,五光十色。对诗情画意的中国人来说,这故事听来是讲得通的……应该承认,神话的根子就在美国大峡谷。”
默茨的推论虽然大胆,却不无根据。现在我们吃惊地得知,在美国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部落中,确实流传着十日神话。徐松石教授经搜集考证,指出:“美洲也有墨西哥境十日浴于扶桑汤谷的故事。又有加利福尼亚沙士太印第安族的十日传说。据谓狗酋达(犬形神人)创造天地日月,造成十个太阳和十个月亮。他们本来是轮流出现的。后来有一个时候,十个太阳白天并出,十个月亮夜里并悬。弄到日间则热似焦火,夜里则冻似寒冰……人民十分痛苦。狗酋达就出来毁灭了九个太阳和九个月亮。然后人类生活得以恢复常态。”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西部的大峡谷,与《山海经》所记“东海之外大壑”方位地貌相合。而流金铄石的大峡谷应为古人眼中日出之处。大峡谷附近的印第安人与中国人有着相似的十日神话传说。至于是否古时来到大峡谷的中国人将印第安人的十日传说带回去,演变成羿射九日的神话,恐怕只能做为默茨的推想而难予考证。
三
《山海经》确实是上古先民认知世界的记录,其囊括的范围大大超越了现今的中国本土。如若不然,《山海经》又如何被分为“海内”、“海外”与“大荒”等不同地域而分别叙述呢?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海内经》和《海内南经》、《海内北经》、《海内西经》、《海内东经》诸篇中,已可以大致看到一个“海内”的轮廓,这个轮廓的东南角已达“会稽”,西北角已达“凶奴”、“东胡”,西南角甚至达到“天毒”(晋郭璞注:天毒即天竺,按指今印度),而东北角则明确记为“朝鲜”与“倭”。
请看:“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晋郭璞为此注曰:“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这就指明《山海经》之《海内北经》提到的“倭”和“朝鲜”即今日的日本和朝鲜、韩国。
既然古时已将日本和朝鲜列于“海内”,那么,《海外东经》、《大荒东经》所到达的地方,必然远于日本和朝鲜。而在日本、朝鲜以东会是哪里呢?答案不言自明,当然应是美洲。
《海外东经》记载的“汤谷”“扶桑”“黑齿国”等,必是美洲,因有其它典籍的记载佐记——《东夷传》载:“倭国东四千馀里,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至也。”
至于《大荒东经》所载“东海之外大壑”,更非美洲莫属。《列子·汤问篇》云“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
而中国古人到达东部如此之远的地方,之所以“质明有信”,并非虚妄,乃是因为有人双脚丈量的结果。
《海外东经》记载道:“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
晋郭璞注:“竖亥”为健行人。清郝懿行注:竖亥右手把算,算当为 。《说文》云:“ 长六寸,计历数者”。而“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这就鲜活地描写出古时测量大地者的生动形象。
“自东极至于西极”,气魄何等之大!“东极”在哪里?《大荒东经》载明,在“日月所出”之处;“西极”在哪里?《大荒西经》载明,在“日月所入”之外。《大荒西经》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和《大荒西经》所载“日月所入”之山各有六处之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人观察一年中不同时间,太阳出升和降落的方位稍有不同。看来,命竖亥测量由东极至于西极的里程,也许与制定历法有关。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与《五藏山经》所记大量山名有所不同,《大荒东经》记载的许多山名都不象中国的山名,比如:
“大荒东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高瞀,日月所出”。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 羝。”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苏门”。
“东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日凶犁士丘。”
上述这些中国人听来很怪的山名,无疑是外域山名的音译,是对当地土人所称山名的直译音录。如果是“海客谈瀛”式的神侃海聊,没必要编些古怪的山名。这倒从一个角度,证明古人确确实实到达了《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地方。
这里应该提到默茨博士在美洲的踏勘中,发现的几处古代石刻。一处位于加拿大的阿尔柏达,一处位于美国北达科他,还有一处在亚利桑那的“四角”(FourCornnrs)。这些石刻文字明显与古玛雅象形文字不属于一个系统,反而与中国商殷之际的甲骨文极为相似,有些文字简直与甲骨文相同。难怪北达科他商业与工业开发署,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曾一度访问过北达科他”;并且在1972年再版的《关于北达科他的种种事实》一书里,附以有关中国人这次探险的记载。④
在北美洲发现的这些古代石刻,很可能就是古人“自东极至于西极”测量大地所留下的遗迹。要知道,“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是一个相当遥远的距离。如果不以古时测量步算(据说旧时丈量土地时左右两脚各向前迈一步为一测量步),仅以普通行走,两步为一公尺计,五亿步当有2.5亿公尺——已有20万公里以上了,其行走距离,早已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可以环绕地球几圈了!如果考虑古人行走时翻山越岭、涉水渡海,不可能以直线行走,“自东极至于西极”距离的记载是可信的。
并且,这项巨大的测量工程,不一定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而是可以由一批同代人或一个部落的同代人便可完成。前些年,上海有位徒步走遍全中国的壮士馀纯顺。笔者虽然没有仔细核查过他的有关资料,但以他经历过的几乎走遍中国大陆上的每一个市县、行走时间历时八年的情况看,他所走过的里程相加,相信已可以绕地球一圈。远古的健行人恐怕日行不止百里,若按日行一百华里计,一年约可走三万多华里,三年便可行走十万华里,足以绕地球一周。从《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两篇记录来看,其叙述风格如出一位亲历者之手。可以推想,古时健行人完成了“自东极至于西极”的壮举,将大荒之东和大荒之西的所见所闻记了下来,并讲述给别人,因此才有了《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
伟哉,华夏先人!
默茨博士研读了《山海经》,并亲自踏勘美洲的山水河流之后,由衷的赞叹:对于那些早在四千年前就为白雪皑皑的峻峭山峰绘制地图的刚毅无畏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低头,顶礼膜拜。⑤ 而今天,我们还赶得上祖先的脚力么?

文章评论